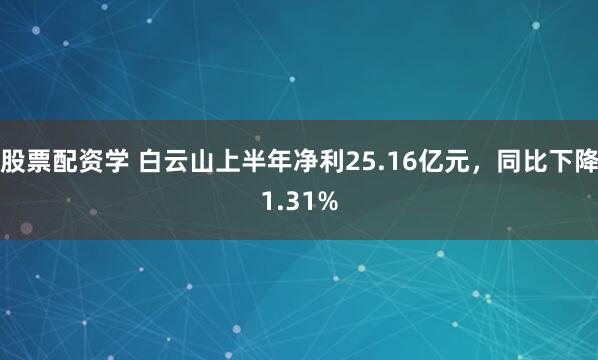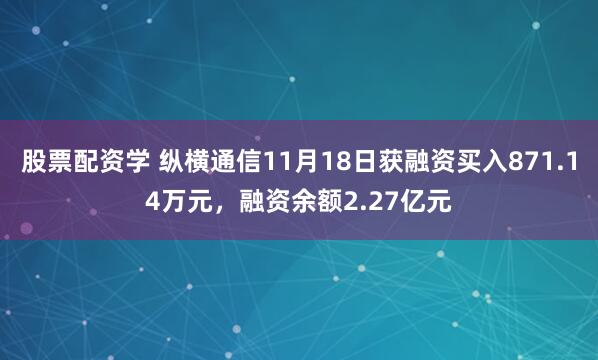天津日报记者 田莹股票配资学
刘挽云
本名刘季赟,天津民间工艺“刻砖刘”第五代传承人,天津美术学院特聘研究生导师,砖刻艺术化、生活化的开创者。代表作品有“洞见”太湖石系列、“解放桥”等。
在机器轰鸣、信息奔流的时代,依然有人选择与青砖为伴,与刻刀共舞。她就是刘挽云,在天津民间工艺领域,与“泥人张”“风筝魏”“杨柳青年画”并称“四绝”的“刻砖刘”的第五代传承人。
她绝非传统意义上的“守艺人”。在她身上,古典艺术的学养与拍卖行里历练出的现代视野交织;工匠世家的执拗血脉与学院派的系统思维共振。她放弃旁人眼中的坦途,选择了一条窄路,不仅要将濒危的手艺从时光深处打捞出来,更要为它在当代生活中找到安身立命乃至蓬勃生长的土壤。在她手中,冰冷的青砖被赋予了温度、呼吸与灵魂,而古老的传承也因此有了更辽阔的心胸与更坚定的心跳。
生在“刻砖刘”世家
一心传承家族技艺
冯骥才先生曾出版《天津砖刻艺术:手稿珍藏本》,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部书稿。上世纪60年代初,冯骥才骑车经过老城里的大街小巷,被老房子上的砖刻吸引。在他眼中,那些砖刻就是繁复华美的艺术品,但也渐渐成为历史的遗存。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,逐一拍下砖刻的照片,并将其所在的地点、在建筑上的位置、雕刻的题材内容记录下来。他还结识了家住西门里、身怀绝技的“刻砖刘”刘凤鸣,得知天津城中很多宅院的砖刻都出自他手,刻砖的一切讲究和诀窍也都在他心上。
清代中期匠人马顺清将依附于建筑的砖刻提升为一门艺术,凭着独创的“贴砖法”闯出了“花活马家”的名号。刘凤鸣是马顺清的外孙,他年纪轻轻便琢磨出“堆贴透雕法”,能在方寸青砖上雕琢出层峦叠嶂的立体山水与栩栩如生的鸟兽精灵。天津的石家大院、广东会馆、北宁公园、大悲禅院等古建筑上,都有“刻砖刘”鼎盛时期的砖刻作品。时光流逝,当刻砖技艺传至刘凤鸣四子刘书儒手中时,古建凋零,砖窑空置,这门辉煌过的老手艺仿佛走到了命运的尽头。
刘挽云是刘凤鸣长子刘书霖的孙女,她自小在这样一个“藏着辉煌过往,却难寻未来”的家族里长大。“四爷爷刘书儒和我的爷爷刘书霖年纪相差很大,我和两位长辈都很亲近,每天都追着他们玩泥巴。”刘挽云回忆,那时候,她的小手总在不停地捏着,一会儿是摇头摆尾的小狗,一会儿是竖起耳朵的小猫,有时还会照着砖刻纹样,捏出简单的缠枝莲。四爷爷在旁边看着,偶尔放下手中的活计指点一句:“耳朵再往前挪一点儿、花瓣的弧度再圆些,才像真的。”
刘挽云对砖刻有热忱,也有天赋,但家里人总说:“女孩子把砖刻当成爱好就好,没必要真扎进这一行。这个活太苦了,责任也很重。”命运的转向,始自她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读书时,到北京一家知名的拍卖行实习。在那里,她结识了范迪安、霍春阳等顶尖艺术家:“那些书画大家们得知我的家世,都鼓励我回天津。他们说,拍卖行少了你没关系,但你不回去,‘刻砖刘’可能就没有了,这是你的责任呀!”一边是拍卖行优渥的薪资和行业经验的积累,一边是家族技艺的未知前路和沉重责任,最终,刘挽云选择了更难走的这条路。
2005年,她向四爷爷提出正式拜师学砖刻,却被拒绝,理由现实又残酷:“这行早就没落了,你干什么都比学这个强,再说现在哪还有能刻的青砖?没有砖,学了也是白学!”四爷爷的阻拦反倒激起了刘挽云的韧劲儿,她偏要找到一块能让四爷爷点头的青砖。
第一次寻砖,她直奔以古建和砖刻闻名的山西,可背回来的青砖却让她碰了壁:山西砖多是“窑前刻”,砖坯需未烧先刻,砖的质地酥软,烧完再刻,一刀下去就崩出坑,不适合天津“窑后刻”对砖体硬度的要求。
江苏知名画家周亚鸣建议刘挽云南下:“南方还有不少家族在修建祠堂,说不定有你要的砖。”这次刘挽云也学聪明了,特意带上了刻刀。来到南方,她发现眼前是另一番景象:大家族修缮祠堂、更新牌楼的需求不断,青砖窑仍在批量烧制,厂房里,工人忙着雕门楼、刻影壁。她拿出刻刀在砖上试刻,青砖质地致密,线条刻得利落不崩裂,甚至因现代工艺改良,密度比祖辈用的老砖更均匀,正符合“堆贴透雕”的要求。她又惊又喜,不仅带回了青砖,还特意拍下视频,记录下砖窑出砖的场景和工人埋头雕刻的状态。
当刘挽云带着青砖和视频站在四爷爷面前时,老人先是愣了一会儿,接着眼底的光一点点亮了起来。他终于明白,刘挽云不是一时兴起,她懂砖刻,爱砖刻,更有不放弃的决心。那块来自南方的青砖成了“敲门砖”,敲开了四爷爷的心门,也让刘挽云如愿成为“刻砖刘”的第五代传承人。
不满足于简单的形制
要把砖刻变为艺术品
那时刘挽云还在北京上学,每个周末都回天津学砖刻。“砖太重,不方便来回带,每天我心里都惦记着没刻完的纹样。”她说。几年过去,四爷爷的身体大不如前,刘挽云终于下了决心,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天津,她说:“也没想前途什么的,就是不能看着两百年的家族手艺断了,现在想来,可能这个决定救了‘刻砖刘’,起码在我这一代守住了。”
刘挽云的砖刻从不是机械地复刻。四爷爷教的是“刻砖刘”的独特技法,她则凭借开阔的眼界,大胆引入现代工具来革新工艺。“女性从事砖刻时指力、体力都是劣势,为此我一直在寻找更趁手的工具。四爷爷只用过角磨机,觉得那已经是最好用的工具了。我尝试使用做玉雕、木雕的各种电动工具,后来发现牙医的气动工具比电动的更稳定,更适合雕刻易断易碎的青砖。”不满足于只是引入雕刻工具,她还主导开发了气电混动集成雕刻工作台,申请了专利。这种工作台能减少雕刻时的震动,让亭台楼阁的廊柱、栏杆等全镂空细节更精准,也解决了雕刻中粉尘污染的问题。对工匠来说,有新型工具的加持,能节省不少体力,大大缩短工期。当刘挽云把用新型工具雕刻出的作品摆在四爷爷面前时,老人感叹:“你比我做得好,真的好,这手艺在你手里活了!”
市场的不认可,是比技法更难逾越的难关。刘挽云坦言,头三年,自己没卖出去一块砖。她再次南下,到安徽与当地人合办砖刻厂,承接古建门楼工程,虽然能带来不错的收入,但这种重复性的工作却不能满足她对砖刻艺术的追求。“砖刻厂的经历让我更明白了自己该走的路,我不想一味地重复一种形制或风格,我要做的是艺术品,想让每一件作品都有思想。”工厂平稳运行后,她返回天津,继续追寻自己的砖刻梦。
“技法是基础,最难的是设计和创意。”她从古典文学里找灵感,也依据米芾《研山铭》的画稿复刻出灵璧石笔山,砖面上山峦起伏、洞穴通透,石纹的肌理清晰可见。她把作品发到朋友圈,没想到,两位搞绘画的老师立刻找上门,愿意高价收藏。“从那以后我想通了,砖刻艺术就是小众,不用追求大众市场,只要找到懂它的人,就可以了。”她把目标客户锁定在热爱传统文化的藏家群体,跟懂的人聊,不用解释为什么一块普普通通的青砖在雕刻之后价值能涨千百倍,好的作品可以让懂它的人一见钟情,这就是知音。
一次喝茶时的偶然发现,为刘挽云打开了砖刻生活化的新赛道。那天她随手把茶壶放在工作台的青砖上,几天后发现,砖面没有一点茶渍,甚至连茶味都没留下。青砖的吸水性和自洁性,让它天然具备了作为茶盘的优势。她刻了一块茶盘,半年后,砖面因吸收茶汤而泛出温润的光泽,像养了多年的茶宠。她开始尝试制作茶盘、壶承、笔山等日用器具。尤其是她为一些紫砂壶藏家定制的壶承,每一块都根据壶的造型、藏家的喜好设计纹样。这些作品很快在藏家圈传开,不少人愿意出高价,再排一两年的队,就为了得到一块专门定制的手工砖刻茶盘。刘挽云感慨:“最普通的青砖,雕刻后比玉还贵,这就是手艺人的价值吧。”
既是“守艺人”
也是革新者
刘挽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“守艺人”,而更像一位追赶时尚的革新者。她深知传统师徒一对一的传承一旦中断,手艺可能就没了,因此她跳出家族局限,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“产教融合”之路。
她与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、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等院校合作,把青砖与刻刀搬进了课堂。不同于传统师徒的口传心授,她针对学生的特点,开发出集成化的“教学包”。其中不仅包含适配教学场景的砖刻工作台、定制青砖材料包与专用工具包,还配套了详细的课程教案与教学视频。这些教学包实用性很强,即便没有砖刻基础的老师,也能对照视频指导学生完成从备料、画稿到基础雕刻的全流程操作。她还推动“刻砖刘”工作室成为高职院校的实践教育基地,让学生参与砖刻项目,在实践中提升技艺,打通了“教学、实践、就业”的传承链条。
“我在南方开工厂多年,深知市场缺什么样的人才,会手工雕刻、会电脑制图、会数控雕刻的全才,在雕刻行业‘一将难求’,所以我们的教学就对准了行业需求;另一方面,在教学中,我也能发现好苗子,重点培养。大家都认为非遗传承是家族秘传,其实有规模的、系统性的教学能更好地传承非遗。”刘挽云说。
谈及当下的非遗传承生态,刘挽云也有自己的想法:“非遗是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,但我们也要认识到,这些技艺是因过去时代人们生活的需求产生的,当代人可能不常用了。传承人首先要做的是守护技艺、精进手艺,其后才是怎样应用。把工艺做到位,再加上用心的创意,得到大家的认可,市场可能慢慢就来了,否则手艺迟早会变味儿。”
这些年刘挽云忙着做两件事:一件是给“刻砖刘”的老作品建数据库,从天津博物馆馆藏的《龙凤呈祥》《四爱图》,到天津清真大寺、老城里徐家大院的砖刻遗存,她带着相机和扫描仪跑遍各处,记录下纹样细节、雕刻技法;另一件,是撰写《天津砖刻》专著,她想把“刻砖刘”的传承谱系、“堆贴透雕法”的核心步骤、天津砖刻南北兼容的风格成因,都白纸黑字地写下来。她说:“以前这些东西都装在四爷爷的脑子里,传给了我,万一哪天我忘了怎么办?写成书,就能留得更久。”她还有更大的梦想,“先把天津的砖刻研究透、写清楚,有机会再把全国的砖刻历史与技法研究一遍,这事现在还没人做,我要是能做完,这辈子就没遗憾了。”
刘挽云用坚韧守住了传统,用智慧浇灌出新芽。就像她刻在砖上的那些纹样,既有祖辈留下的感觉,又有属于这个时代的气息。这,或许就是传承最好的状态。
刘挽云访谈
一代代人不断革新
才形成了好的传统
记者:您认为怎样才能把传承这件事做好?
刘挽云:最初我四爷爷反对我学砖刻,是认为这门手艺没用了,看不到前景。我找青砖,展示南方的砖刻产业,不是为了证明它能挣大钱,而是为了证明现代社会依然有人需要这门技艺。这是一种存在价值的证明,是给我四爷爷信心,也是给自己信心。非遗传承的前提,是传承人从内心认同它的文化价值、艺术价值,并找到它能与当代社会连接的那个点——可以是市场需求,也可以是教育价值、审美价值,甚至是情感价值。我先证明了它“活着”,然后再去思考如何让它“活得好”。顺序不能乱,心态不能急。
记者:您如何看待传统技法与现代技术之间的关系?
刘挽云:什么是传统?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模具,它本身就是一代代人不断革新、积累的结果。当年天津城的老匠人马顺清发明了“贴砖法”,我太爷爷刘凤鸣发明了“堆贴透雕法”,这些在他们的时代,也是创新。工具是为人服务的,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创意、实现工艺精度。我四爷爷说,“你比我做得好了”,他夸赞的不仅仅是我用了新工具,更是我在新工具的辅助下,实现了他们当年想实现却难以达到的极致效果,比如更精细的镂空、更稳定的刻画。这种超越是对他们技艺的真正继承和发扬,是对传统最大的尊重。如果固守老工具而让手艺停滞不前,甚至因为难度太大,做得远不如前人,那才是对传统的辜负。
记者:您如何把握艺术追求与商业生存之间的平衡?
刘挽云:我的平衡之道很清晰,就是“以商养艺,分层对待”。我把业务分得很开:一部分是商业板块,比如工厂承接的古建工程,要符合市场规律,要考虑成本、效率、客户需求,它是我和我的团队生存的基础;另一部分是艺术创作板块,这是纯粹的个人表达,可能耗时数月,不考虑市场接不接受,只追求艺术上的极致,我不求靠它挣钱,它更像是我的学术研究和个人修行。幸运的是,当商业板块做得扎实、艺术板块的成果逐渐被藏家认可后,就会形成良性循环——商业收入支撑艺术探索,艺术上的突破反过来又能提升整个品牌的价值和商业项目的品位。关键是不能本末倒置,不能为了迎合市场而牺牲掉手艺的根和魂。
记者:您对自己的定位,是艺术家还是手艺人?
刘挽云:我从不敢自称艺术家,只能做一个“艺术化的工匠”,以传统技法进行艺术表达。既好看又有艺术思想的作品,就是好作品,商业是让这个好作品能被更多的人看见、让手艺得以延续的手段。如果一心只想挣钱,手就会抖,眼就会花,做出的东西必然匠气、俗气股票配资学,最终连商业价值也会失去。
永华证券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